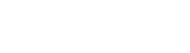贺云翱: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
图一 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位置示意图
一、地理位置
南朝坛类建筑遗存所在的钟山位于南京城的东北郊(图一、二),古称金陵山。汉代称钟山,东吴称蒋山,东晋时因山体露出红紫色页岩,称紫金山。南朝时又因其在都城建康之北,一称北山。它是宁镇山脉地区最高峰,东西长约7、南北宽约3公里,面积20多平方公里。山势略呈弧形,弧口朝南;山有三峰,东西并列似笔架。中为主峰(北高峰),海拔448米。东为第二峰(小茅岭),海拔350米。西是第三峰(天堡山),海拔250米。
图二 南京南朝钟山坛类建筑遗存位置示意图
一号坛位于钟山最高峰南面山腰处向南延伸的一座山嘴的顶部,北依钟山主峰,坐北朝南。山嘴东、西二面坡度陡峻,左右形成两道山谷,谷水环抱山嘴,流入正对祭坛山梁的紫霞湖中[1],从紫霞湖正面观察,呈金字塔状的山势成了祭坛的基座(图三)。
二、布方及地层
在第一次发现石墙后并开始勘探工作前,我们就以这道石墙(因其为一号坛东面第二道坛墙,故编号为NZJ1EQ2)最南边一块巨石的东南角作为0点,分别向南、向东延伸10米,作为第一个探方(编号T101),然后再以T101南边线向正西方向延伸的线作为X轴,T101东边线向正北方向延伸的线作为Y轴,每个探方长、宽均为10米。随着工作面积的扩大和遗迹现象的增多,探方数不断增加,最后一号坛总布方数达到81个(T101~T909),但坛体局部地区因生长着古树名木或分布民国时期的碉堡及公路而不能发掘,故实际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图四)。
整个遗存区的地层堆积情况比较简单,由于遗存分布于茂密的丛林区,所以地表覆盖着一层厚0.1~0.2米的树木枝叶腐殖层。该层以下为扰乱层,一般厚0.1~0.2米,但在一些沟、坑中,深度可达1米左右。扰乱层内可见近现代玻璃片、塑料制品、民国时期在此修筑公路和碉堡时丢弃的手榴弹、水泥砖块等,也有极少量明清或宋元时期的瓷片。清理扰乱土层后,其下即为文化层。文化层一般可分为两层,上层是祭坛建筑废弃以后倒塌、坍毁的堆积物层(夹杂石片和瓦砾、断砖等),下层是祭坛建筑遗迹本身。祭坛遗迹之下即为山体基岩。
图三 一号坛所在地形图(箭头处为一号坛所在的山嘴顶部,左右为山谷)
图四 一号坛发掘布方图(斜线处为未发掘区)
现以T601北壁剖面为例(图五:上)。T601位于一号坛最东侧,地层堆积呈坡状。
第一层:表土层。厚0.1~0.2米。灰褐色腐殖土,内夹树叶、砖块、石块等。
第二层:灰土层。厚约0.2米。为扰乱土层,内有民国时期的手榴弹、水泥块、六朝断砖等。
第三层:石块层。石块和泥土中夹杂六朝断砖、少量瓦片等,还出土了一件石雕莲花纹器座残件。
第四层:建筑遗迹层。包括各道坛层的石砌护墙(NZJ1EQ2、NZJ1EQ3,NZJ1EQ4、NZJ1EQ5)和护墙之间构成的坛层均在这一层位。各坛层石墙之下用纯净的黄砂土垫底。为防止护墙倒塌,我们仅对NZJ1EQ2下部做了局部发掘,发现其所垫黄砂土厚度超过0.4米,黄砂土之下即为基岩。
图五 上:NZJ1T601北壁地层剖面图 ①表土层:腐殖土、现代层 ②灰土层:小石头、灰土、瓦、砖等 ③乱石层:石头、瓦片、黄土、瓷片等 ④遗迹层:四道墙体及四个层面;下:NZJ1T609北壁地层剖面图 ①表土层:腐殖土、现代层 ②灰土层:石片、后代杂物 ③石块层:石块、石片、砖、瓦、石雕莲花座 ④黄土层:内夹细小石片、砂 ⑤小石片层:黄土少、多石片 ⑥遗迹层:三层墙体及三个层面。
再以T609北壁剖面为例(图五:下)。T609位于一号坛最西侧,地层堆积呈坡状。
第一层:表土层。厚0.1~0.2米。主要是腐殖土和树叶等。
第二层:灰土层。厚约0.2米。内含石片、断砖等。
第三层:石块层。厚0.3~1.44米。内含大量石片、石块、六朝断砖、少量瓦片等,这一层出土4件石雕莲花纹器座。
第四层:黄土层。厚0.3~1.7米。这一层作不连续堆积状,仅分布在探方的西侧。内夹细小石片、砂土等。
第五层:小石片层。厚0.3~0.8米。地层内黄土较少,石片很多,十分纯净。
第六层:建筑遗迹层。遗迹有NZJ1WQ2、NZJ1WQ3、NZJ1WQ4等。
石护墙之下垫以黄砂土和细石片,经过NZJ1WQ4下部作探沟解剖,发现其垫层厚度超过1米,因防石护墙倒塌未再下挖。
三、遗迹
发掘区的主要遗迹为一座由石墙围护的祭坛坛体及东、西、南三面各四个依次降低的坛层(图六)。
坛体作正南北方向。北面依山,并被公路所压。东、南、西三面从高向低分别建造五道石砌护墙(每面从上到下各墙依次编号为NZJ1EQ1-NZJ1EQ5、NZJ1SQ1-NZJ1SQ5、NZJ1WQ17-NZJ1WQ5),石护墙顺山坡砌成,北端山坡高而墙低,南端山坡陡而墙高,但各墙上口大约保持在一个平面。石护墙之内下填块石和黄土,表面填以细砂、细石片和纯净黄土,形成主坛体及低于主坛体的四个坛层,即一号坛坛体的东、南、西三面四个坛层内外各被石墙所围护。
图六 NZJ1遗存总平、剖面图
石构坛体及各坛层护墙,除东面第二道护墙的一部分祼露于地表树丛中外,其他各墙在发掘之前均掩埋于倒塌的乱石或土层之中,其中南面石墙的西段由于民国时期在此构筑碉堡而被毁损严重,其他各墙因地势陡峻易于倾倒、历年雨水山洪冲刷等原因多有倒塌或局部缺损。但经发掘,其主坛体基本保持完好,各坛层的原有格局也大体完整(参见表一)。
表一 一号坛坛体及坛层石护墙遗迹数据表
单位:米
东面的五道石构护墙,第一道墙北段保存较为完好,长约38.5米;第二道墙保存状况最好,残长约76米,这两道护墙之间构成了第一个坛层,宽2.7米;第三道墙残长约77.8米,它和第二道护墙之间构成第二个坛层,宽1.4米;第四道墙北段缺失,残长约54米,它和第三道护墙之间构成第三个坛层,宽2米;第五道墙保存较好,残长约95.3米,它和第四道护墙之间形成的坛层宽5.3米(图八、九)。
图七 NXJ1T609Q2、Q3、Q4遗迹侧视图
西面的五道石构护墙出土情况是:第一道护墙坍塌殆尽,仅在T809内发现一段,残长3.6米;第二道护墙保存较多,残长67米,这两道护墙之间构成的第一个坛层宽2.7米;第三道护墙除北部一段残缺外,其余保存尚好,残长57.4米,它和第二道护墙之间构成的坛层宽1.5米;第四道护墙情况同于第三道护墙,残长60米,它和第三道护墙之间构成的坛层宽2.5米;第五道护墙除南面一段尚存外,余已塌毁,残长约28.5米,它和第四道护墙之间构成的坛层宽2米(图一〇、一一)。
南面五道护墙分为两段,中部被一条5米宽的登坛阶道隔断。但作为坛体的一面,我们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一面的西段由于民国时在此构筑一座水泥碉堡,导致第一、二道坛体及坛层护墙多处被破坏。而第三、四、五道护墙上部堆积的地表上又生长着一棵古树名木,无法全部发掘。已发掘的第一道石构护墙残长11.6米,第二道护墙东段保存较好,残长约65米,这两道护墙之间形成的坛层宽2.7米,这一坛层南段近中部登坛阶道处保存有铺砖的遗迹(图一二);第三道护墙残长约16.5米,它和第二道护墙之间形成的坛层宽1.5米;第四道护墙东、西两端保存较好,残长17.3米,它和第三道护墙之间形成的坛层宽2米;第五道护墙东、西两段不在一条直线上,其中东段残长38.4米,它和第四道护墙之间构成的坛层宽5.3米,而西段护墙比东段护墙内收,残长10米,它和第四道护墙之间形成的坛层宽1.5米。
图八 一号坛东面第2、3、4道石护墙及坛层遗迹(由北向南摄)
据上所述,在坛体东、西、南三面各四个坛层中,第一个坛层的宽度三面相同,皆为2.7米:第二个坛层的宽度面基本相同,为1.4~1.5米;第三个坛层的宽度,东、南两面相同,皆为2米,但西面稍宽,为2.5米;第四个坛层的宽度东、西两面差异较大,东面宽5.3米,而西面宽仅2米,南面情况略复杂,其东段同于西面宽度,也为5.3米,而西段则接近西面,宽1.5米。
由东、西、南三面第一道坛墙构成的主坛坛面东西宽64.8、南北长64(东)~69.3(西)米,因坛体北端被公路破坏,实际长度无法确定。但根据公路宽度(宽6米)和修筑时对山体及一号坛与二号坛之间的阶道的破坏情况分析,坛面南北长度已无可能增加。也就是说,主坛面大体上近于方形。
在构筑坛层的石护墙中,以第二道墙体最为高大,应为主墙(图七)。以坛体东面第二道护墙(NZJ1EQ2)和第三道护墙(NZJ1EQ3)为例:前者残存最高处3.17米(在T601内),而后者残存最高处仅0.8米(在T401内)。第二道护墙所用石材较为硕大,最重的将近2吨,石材加工程度一般,多利用自然劈裂面加工而成。墙体垒砌技术较为简单,石块之间不用任何粘接材料,仅以石块之间的上下左右交错关系加强牢度。但各墙均取正南北方向,多个坛层及护墙高低错落,壁立于陡坡之上,尤其是祭坛东南、西北两角都用巨石构角,其上部坛面(此处坛体石护墙倒塌严重,但角部巨石、坛体填石及坛面仍有保存)和最下一道石护墙之间的垂直高度达到11.45米,所以整个祭坛显得高大雄伟。
经在T509内做局部解剖,主墙内从下向上分层充填着纯净的人工砸碎的石块、碎石片和黄土,充填物厚度超过4米,随着山势的下降,石护墙不断增高,护墙内所填石、土厚度也随之增加,在坛体南部,坛体充填物厚度超过10米。根据护墙高度和坛体面积推算,整个坛体体积超过40000立方米,填石、填土的工程量浩大。
图九 一号坛东面第5 道石护墙遗迹(由南向北摄)
图一〇 一号坛西面第2~4道石护墙遗迹
图一一 一号坛西面T609内第2~4道石护墙及坛层
在祭坛表面,又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了4个小台。小台的表面曾受到后代程度不等的破坏,但台的整体形状还大致保持。各台基本上都作方形覆斗状,4个小台中较为高大的一个(编为一号坛1号台,NZJ1t1)位于主坛的南部正中(图一三),其他三个位于1号台的北面,呈东西一线排列(由东向西分别编为NZJ1t2、NZJ1t3、NZJ1t4)。小台皆取正南北方向,作中轴对称布置。其中1号台上部边长约13、下部边长约20、残高约2.5米。其他三台上部边长约12、下部边长约18.5、残高约1.5米。经对4个小台做钻探,其中1、2、4号台台面以下0.5~0.6米深时就大部是填充的碎石块,只有3号土台一直钻探到3米多深仍是黄土,个别孔内黄土中夹有白土。在1号台下部北侧、2号台南侧、4号台南侧都发现有较多的断砖堆积,局部还保留了铺砖的迹象。
图一二 一号坛南面第2道石护墙及台阶西侧坛层上铺砖遗迹
T303、T304、T403、T404交汇处的1号坑(NZJ1k1)属于古代遗存,其位置在1号土台正东,大体与1号土台东西并列,平面近于“十”字形,南北和东西基本等长,为5.2、最深处2米。坑底部凿山体基岩而成,其开口与一号坛面在一个平面上(图一六)。
一号坛的南面中部,顺坛体坡度砌造一条方向为正南北的石阶道路(NZJ1L1),残长约20、宽5米。其结构是顺阶道东、西两侧用不甚规则的石条砌护边,其中西侧护边保存较为完好,东侧护边多被毁坏,仅在上部残存的几层石阶东边留有几块压边石。阶道做法是:每几层石阶之间做出一层石铺平台。石阶和平台出土时多已毁坏,保存较好的共有三组,第一组石阶在祭坛上部,由三层石阶和一层平台构成(图一四);第二组石阶在祭坛南坡中部,尚存四层石阶(图一五)和一层平台,但平台台面上的铺石已不见;第三组在祭坛下部,仅见3层石阶。这条石阶道路是已经发现的登上一号坛的惟一通道。
四、遗物
表土层和灰土层中出土遗物主要是六朝时期的断砖、瓦片,极少量的宋代黑釉瓷片、明清时代的青花瓷片及民国时的手榴弹、玻璃瓶等。
石片层和瓦砾层中出土了一批时代特征明确的六朝遗物,主要有砖、板瓦和筒瓦、莲花纹瓦当、青瓷片、莲花纹石座等。瓦和瓦当的分布较有规律,它们比较集中出土于一号坛的南侧中部登坛石阶附近。分别介绍如下:
1.砖 多为灰砖,砖型较大,一般规格为长34、宽17、厚4厘米,也有体型稍大者。正、反面饰绳纹,有的端部模印或戳印表示方位的文字。标本T304③:4,残长25、宽16.6、厚3.6厘米,端面模印“西乇”二字(图一七、二七:左);标本T105③:1,残长15、宽22.5、厚5.5厘米,端面戳印“东乇”二字(图一八、二七:右)。
2.筒瓦和板瓦 多为灰陶或灰黄陶。筒瓦规格为长27、直径14、厚0.1~0.15厘米,瓦内面印麻布纹。板瓦无完整件,一般在瓦身正面多见瓦楞纹或纵向刮削的痕迹,瓦身反面印麻布纹。
3.瓦当 一号坛共出土瓦当110枚,但多残破。出土的所有瓦当当面上均饰莲花纹。莲花有8、9、10、11瓣等之分。瓦当边轮较高。当面直径一般在13~15厘米之间。依其造型之不同,约可分为六型。
I型多黄灰陶质。当面饰8瓣莲花。莲瘦削而劲挺,莲瓣之间的分隔线顶端作三角菱形,三角舒展有力,中央莲蓬周边凸起,莲蓬上饰9颗莲籽。莲花周边有一圈凸弦纹。标本T102③:17,当面直径13.8、边轮宽1、高0.9厘米(图一九、二八:1、二九:1)。
Ⅱ型多黄灰陶质。当面饰8瓣莲花,瓣形长而较宽,莲瓣之间的分隔线顶端也作三角菱形,但三角较短,两侧角作陡直竖起状,中央莲蓬略低平,周有一圈凸弦纹,莲蓬上饰7颗莲籽,莲花周边不见弦纹。标本T901③:8,当面直径13.4、边轮宽1、高1厘米(图二o、二八:2、二九:2)。
Ⅲ型多黄灰陶质。当面饰8瓣莲花,莲瓣饱满,瓣之间分隔线顶端作肥大的“T”字形,中央莲蓬凸起,上饰9颗莲籽,但莲籽较为模糊。莲花周边不见弦纹。标本1901③:7,当面直径13.4、边轮宽1.1、高1厘米(图二一、二八:3、二九:3)。
图一三 一号坛坛面的1 号黄土台
图一四 第一组石阶遗迹
图一五 第二组石阶遗迹
图一六 1 号坑(NZJK1)平、剖面图
IV型多黄灰陶质。当面饰8瓣莲花,瓣体短而较劲挺,瓣尖部和瓣之间分隔线顶端都作三角箭头形。莲蓬小而凸起,上饰7颗莲籽。有的在莲花和边轮之间有一道凸弦纹。标本T105③:2,直径1.4、边轮宽1.1、高0.7厘米(图二二、二八:4、二九:4)。
V型青灰陶质地。当面饰10瓣莲花,瓣体瘦削而饱满,瓣间分隔线顶端作四尖或五尖菱形。莲蓬较为低平,上饰8颗莲籽。莲花与边轮之间饰一周凸弦纹。标本T609③:8,直径14、边轮宽1、高1厘米(图二三、二八:5、二九:5)。
VI型黄灰陶质地。当面饰8瓣莲花,莲瓣较为饱满宽大,瓣之间分隔线顶端和莲瓣尖之间以间断弧线相连,在莲花纹周围形成一道连弧状纹。莲蓬周边突起但中部稍凹,上饰8颗莲籽。标本T102③:20,直径14、边轮宽1.4、高0.9厘米(图二四、二八:6、二九:6)。
4.青瓷片 一号坛不同探方内出土了10余件瓷片,胎质多较粗,器表着青釉或青黄色釉,釉面开细片,有脱釉现象。器头有罐、碗(盂)、盘口壶等。
标本T105③:4碗(盂)口沿及腹部断片。浅褐色胎,质较粗松。圆唇,壁上直下弧,内外施黄绿色釉,釉不及底,局部有流釉现象。
标本T307③:1为盘口壶颈部残片。灰白胎,胎质较松,有气孔。 矮颈,内外施黄绿色釉,釉面开细片,釉面光亮局部有脱釉现象(图二五)。
标本T605③:1碗(盂)底残片。黄灰色胎,胎质粗松。矮圈足,足及器身内外皆无釉,看似陶器。足底有线切割痕迹。足直径4.6、高1.1厘米(图二六)。
5.石雕莲花纹器座 共出土13件。分别见于T201(2件)、T501(1件)、T601(1件)、T602(1件)、T609(6件)、T709(1件)。
这批莲花纹石座的出土地点东、西呼应,且大都位于第二道护墙之外。从出土现象分析,它们均不属于原生地的遗存,而是来自另一地点。在大多数石雕莲座出土地点之上,恰好分别是一号坛坛面上的第2号土台和第4号土台,因此我们认为它们可能原是置于土台上的器座,在祭坛被废弃后而滚落到了主坛面下的坛层上,而且在2号台和4号台上也确实分别出土了各1件器座(T109③:1、T609③:12),下面择要介绍。
标本T609③:1,青石质。平面作圆形,平底,器身从下往上渐内收,溜肩,侧视似馍首状,全身一周饰8组宝装复瓣莲花,莲花作覆莲状。器上部作圆台式,台中部雕出一长方形榫状结构。底部直径13.3、高10.8、上部圆台直径7、高1、台上榫长3.2、宽1.5、残高0.6厘米(封二:1,图三〇:1)。
标本T609③:12,青石质。略残。造型同上,但器身从下往上内收不甚明显,耸肩,装饰风格及其他做法同于上器。底部直径13.2,高10、上部圆台直径8、高0.8、台上榫长2.9、宽1.9、残高0.7厘米(封二:2,图三〇:2)。
五、几点认识
(一)时代
一号坛除扰乱地层出土极少量宋代以后的瓷片外,凡文化层出土遗物都具有南朝的时代特征。
图一七 一号坛出土模印“西乇”铭砖
砖、瓦
绳纹砖和麻布纹瓦在南京市六朝墓葬或市区六朝地层中常有出土。模印“东乇”“西乇”的铭文砖在南京梅花山南朝早期墓[2]、清凉山六朝石头城遗址及城区六朝地层中也偶有发现。根据我们近年对南京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六朝瓦当的系统研究,莲花纹瓦当最早在南京虽然出现于东晋时期,但大量流行要到南朝。这里出土的瓦当既保留了一定的东晋时代的风格(如边轮较高,当面周边饰一圈凸弦纹,莲瓣之间的分隔线顶端花卉呈三出叉或四出叉,瓦当上的莲瓣普遍较为瘦削等),同时也具有南朝的一些特点(如当面周边的一道弦纹渐次不甚明显,莲瓣之间的分隔线顶端花卉逐步简化为“丅”字形,莲瓣开始变肥厚等)。因此,把出土的砖、瓦类文物的时代定为东晋后期到南朝早期是较为适宜的。
图一八 一号坛出土戳印“东乇”铭砖
2.瓷片
瓷片标本中盘口壶颈部较矮,表明该器器身较低;碗类器多见假圈足,圈足底部常有挖削凹弦纹的做法;一些器底内出现多粒泥托珠垫烧印痕;器物以素面为主,少量有弦纹装饰;釉面以青黄色为主,多见细开片,胎釉结合程度一般逊于东吴、西晋时的同类器等。这些都是东晋晚期至南朝偏早期的特征[3],所以我们把这批瓷器标本的时代也定为东晋晚期至南朝早期。
3.石雕莲花纹器座
一号坛遗址出土的石雕器座,由于其上装饰着宝装复瓣莲花纹,对其时代必须做专门的讨论。饰宝装复瓣莲花纹的台座式器物,过去在南京及江南地区一般都见于萧梁时代,如南京栖霞山石窟的梁代宝装复瓣莲花佛座、江苏丹阳及南京地区所见南朝梁代帝王陵墓神道华表顶上的宝装复瓣莲花盘、南京东郊灵山梁代大墓出土的饰宝装复瓣莲花的青瓷莲花尊[4]等,因此,这容易使人们把这批器座的时代定为南朝中晚期。其实,根据已有资料,宝装复瓣莲花装饰纹样在南京及附近地区早在东吴时代就已经出现,如南京雨花台长岗村五号墓出土的一件釉下彩盘口壶上装饰的佛像,其莲花座就作宝装复瓣莲花式样[5],饰宝装复瓣莲花的南朝帝王陵神道华表顶盘,虽然目前所见最早一件属于梁代初年的梁文帝萧顺之陵,但是,南朝帝王陵神道石刻制度(包括麒麟或辟邪、神道石柱即华表、石碑一组)形成于宋武帝刘裕初宁陵,后来南朝历代帝王陵都予沿用[6],尽管目前刘宋初宁陵及丹阳齐代诸帝陵前仅存石雕麒麟,但只不过它们的华表与石碑早已亡佚而已。如果今后在刘宋和萧齐的帝陵神道上做发掘,当会发现南朝早期的饰宝装复瓣莲花的华表顶盘[7],此外,类似的宝装复瓣莲花纹也见于当时北方地区,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有公元420年题记的169窟无量寿佛龛第6号龛主佛即结跏趺坐于宝装复瓣莲花台上[8]。为此,结合一号坛同地层出土的其他遗物,我们认为这批石雕莲花纹器座应是属于南朝偏早期的遗物。
图一九 Ⅰ型莲花纹瓦当(T102③:17)
图二○ Ⅱ型莲花纹瓦当(T901③:8)
图二一 Ⅲ型莲花纹瓦当(T901③:7)
图二二 Ⅳ型莲花纹瓦当(T105③:2)
图二三 Ⅴ型莲花纹瓦当(T609③:8)
另在《宋书》、《建康实录》、《通典》等有关史书中[9],都有刘宋大明三年(459年)移北郊坛于钟山的记载,而且有一些史书中直接指认刘宋北郊坛遗存就在钟山定林寺山巅,而据我们近年调查,古定林寺遗址恰好在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西侧下部山谷中[10]。
图二四 Ⅵ型莲花纹瓦当(T102③:20)
图二五 青瓷盘口壶颈部残片(T307③:1)
综上所述,我们把一号坛的时代定为南朝早期的刘宋时期。
(二)性质
1.结构
出土的一号坛及其主坛面上加筑的4座小土坛,其平面形状都近于方形,依据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及祭地之坛皆作方形的文献记载,这处遗存当与祭地有关。4座小土坛或可称“重坛”[11],一号坛南面正中的石阶道路当为“南陛”[12],坛应为南向[13]。坛上的1号坑或是由人工开凿的用于祭海的设施[14],出土的瓦当、板瓦等,可能与“坛门”建筑有关[15]。
图二六 碗(盂)底部残片(T605③:1)
图二七 左:一号坛出土的模印“西乇”铭砖拓片(T304③:4);右:一号坛出土模印“东乇”铭残砖拓片(T105③:1)(均为1/3)
2.地形
按照中国古代地坛的建筑要求,坛周必须有水泽之象,而一号坛虽然地势较高,但其建造于地势前凸的山嘴之上,左右两侧及前方低处都有峡谷山溪和小湖泊相绕,大体具备了“地处水泽之中”的象征条件,即这座坛在营造时,将所处的地形地势也纳入了整体设计之中,使之具备了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此外,据文献记载,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始立的北郊坛位于覆舟山之阳[16],陈朝的北郊坛在幕府山之阳[17],而这次发现的坛类建筑遗存地处钟山之阳,它在地理位置上符合六朝时期北郊坛择地的一般特征。
3.方位选择
六朝首都(东吴时称建业,东晋、南朝时称建康)的规划采阴阳、四象、八卦、天干、地支思想,在南、北郊坛的方位选择上也是如此。据《晋书·礼志》记载,东晋太兴二年(319年)始立的南郊坛位于“南郊巳地”,即宫城的东南方位,由郭璞“卜立之”,贺循定制度。而《宋书·礼志》讲到都城北郊坛移于钟山时,“与南郊相对”,即其应当是在宫城之东北方位(丑地),而此次发现的坛类建筑遗存恰好是在南朝宫城的东北方位上(参见图一),与文献记载相合。
图二八 一号坛出土莲花纹瓦当
1.I型(T102③:17)2.Ⅱ型(T901③:8)3.Ⅲ型(T901③:7)4.IV型(T105③:2)5.V型(T609③:8)6.VI型(T102③:20)(均为1/5)
4.出土遗物
坛上出土遗物除建筑材料外,主要是少量瓷片和石雕莲花座。瓷片不仅数量少,而且种类较单一,只有盘口壶、罐和碗(盂)三种,与南京地区同时代墓葬中出土的青瓷类随葬品相比,它们的质地显得明显粗松,脱釉严重,有的无釉,看上去如同陶器,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我们认为可能与当时祭祀天地的理念有关,《宋书·礼志》中述及郊祭用器时,提到用陶豆、瓦樽、瓦圩(盂)等“酌毛血”或“盛酒”、“斟酒”[18],依当时人所言“郊望山渎,以质表诚,器尚陶匏,籍以茅席”[19],即郊祀所用器物要求尽量接近自然,不求精美豪华。这种追求天然、朴素的理念还体现在坛体构造特征和用瓦风格上,如坛体只用黄土和石两种材料,石料加工也相当粗糙,所用砖、板瓦、瓦当等与城区六朝地层甚至墓葬出土的同类材料相比,也同样显得不够精致,如瓦当多为黄灰色,胎质较粗,而城区出土的同时代瓦当却多为青灰色,且质地坚硬。这些具有共同特点的遗存现象,反映出一号坛所具备的内在统一的建筑设计思想和使用意图。
出土于2号、4号土台及其附近坛层上的石雕莲花器座,造型较为特殊,我们认为它们应是“神座”,《晋书·礼志》载当时北郊坛共祀四十四种神,“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翳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塘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这些所祭祀的神主在坛上应有“神座”[20],而现在发现的这些石雕莲花纹器座造型下大上小,顶部还有凸榫,可以插置木质的神主牌位。惟一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些器座上为什么雕有佛教莲花图案。按说北郊坛所祀诸神为中国传统的“神祇”,它们的神主能否置于饰有佛教图案的神座之上,值得探讨,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佛教盛行,据史载,东晋时期,首都建康有著名佛寺38处,至刘宋时,增至98处[21],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世家贵族奉佛成风,佛教莲花图案随之也普遍使用,如帝王的神道华表、建筑用砖、宫殿、衙署所用瓦当、瓷器装饰等都无不见其身影。实际上,六朝时期中国传统的道教人物与佛教莲花发生关系,或将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的道教信仰相结合的艺术实例并不少见[22],即使是中国传统的道教神仙人物造像,也或者用佛教莲花作台座、背光等。在湖北鄂州出土的一面西晋时代的铜镜上,有一侧身趺坐人物,戴高冠,冠后飘起一长带,蓄长髯,人物作中国传统的道士或神仙装,但却坐在莲花座上,类似的形象也见于日本出土的时代相近的铜镜上[23]。南京还发现过东吴到西晋的青瓷器上装饰着坐莲花座、肩生双翼的似佛似道的艺术形象。道教人物坐莲台的图案亦见于北朝时期的高句丽地区[24]。四川成都近年出土的一尊南朝道教造像,其头光作莲花式,与佛教造像颇为雷同[25],以上这些实例足可证明,在佛教思想盛行,道、佛互为交融的六朝时期,用莲花台座作为中国传统神祇的神座是毫不奇怪的。
图二九 莲花纹瓦当拓片 1.Ⅰ型(T102③):17)2.Ⅱ型(T901③:8)3Ⅲ型(T901③7)4.Ⅳ型(T105③:2)5Ⅴ型(T609③):8)6Ⅵ型(T102③:20)
图三○ 1.一号坛出土石雕莲花纹器座(T609③:1)2. 一号坛出土石雕莲花纹器座(T609③:12)(均为1/6)
5.文献记载
从成书于梁代的《宋书》,到唐代的《通典》、《建康实录》,宋代的《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直至元代的《至正金陵新志》、《游钟山记》等,都记载着刘宋孝武帝时移北郊坛于“钟山北原(有的史书上作“京”)[26]道西”或“钟山定林寺山巅”的史实,相关记载流传有绪,应可从信。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钟山一号坛建筑遗存应为南朝刘宋孝武帝[27]大明三年(459年)所建的国家北郊坛遗存。
(三)学术意义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1949年以来的考古工作一直比较集中于地下墓葬的发掘和研究,迄今尚未发现和发掘过一处与国家都城建设有关的地面建筑遗存,钟山坛类建筑遗存的发现,弥补了这一不足。它作为国家都城礼仪建筑物之一,所反映在方位、布局、结构、用材、施工方法、设计思想等方面的各种现象,为研究六朝的地面文物制度和建筑风格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
祭祀天、地是我国古代封建帝王独占的权力,南北郊坛也因此成为西汉以后都城建设中地位最为崇高的礼仪性建筑。关于北郊坛即地坛的建筑实物,过去能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实物是明嘉靖九年(1530年)初建,后清代屡加重修的北京地坛[28],更早的实物一直阙如。据文献记载,我国都城北郊坛礼仪制度始于夏、商,但语焉不详。其实,直到西汉时代,皇帝祭地仍主要在汾阴后土祠(宫),至东汉光武帝时,才正式于洛阳城北四里立方坛;晋武帝时,帝祠南郊,“方泽不别立”;东晋初“地祇共在天郊”;晋成帝时方于覆舟山之南立北郊坛[29],可见,从西汉到南朝早期,北郊坛制度始终还处在变化之中。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作为迄今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国家北郊坛遗存,对认识我国早期北郊坛礼仪制度无疑具有直接的帮助。况且,尽管文献对早期北郊坛有简单的记载,但一直缺乏实物以供学者解析和研究,这次发现的北郊坛遗存弥补了研究资料的不足,为进一步认识早期郊祀礼仪形式和内涵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同时,六朝作为我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大转折的时期,其郊坛建筑和郊祀礼仪也存在着既继承从先秦以来的早期祭坛建筑及祭祀活动的某些传统,同时,又具有隋唐以后封建国家郊坛制度的一些特点,它既可映证某些文献记载,又有一些与文献记载不完全一致的地方[30],这些对研究古代郊祀礼仪制度的发展特别是汉唐之际的演变过程都应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这一建筑遗迹包括二号坛和附属建筑区,规模庞大,布局保存较为完好。它对研究我国早期坛庙建筑史具有特定的意义。一号坛出土的瓦当时代较为明确,对研究六朝时期的瓦当分期和装饰风格也有一定的价值。
(本文执笔者为贺云翱、邵磊;本考古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徐苹芳、魏正瑾、谭跃、王学智、刘伯生、吴建民、龚良、车广锦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致谢意!)
参考文献:
[1]紫霞湖扩建于民国年间,但据文献记载,此地古有“落叉池”,见《首都志》(中正书局,1935年版)卷二《山陵上》引《六朝事迹》。从地貌上看,祭坛所在的山梁两侧峡谷溪水皆交汇于此,本应有湖。
[2]资料存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和明孝陵博物馆。
[3]魏正瑾、易家胜《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分期探讨》,《考古》1983年第4期;刘建国《东晋青瓷的分期与特色》,《文物》1989年第1期。
[4]资料存南京市博物馆。另见南京市文化局、文物局主编《南京文物精华》(器物编)第128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5]易家胜《南京出土的六朝早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文物》1988年第6期。
[6]南朝帝王陵神道石刻制度形成于刘宋初年,如刘裕初宁陵陵前现尚存麒麟一对,原有墓表(一称华表、石柱)已佚,《建康实录》卷十三载大明七年(463年)夏四月,“大风折初宁陵华表。”足可为证。另《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南史·豫章文献上传》述及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神道上也有墓表、麒麟等石刻。《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葬宣贵妃,墓前立石柱(墓表)。
[7]南朝帝王陵前墓表(华表)因体形修长,易于损坏。如《建康实录》卷十三载刘宋大明七年(463年)大风折断宋武帝刘裕初宁陵前华表,《建康实录》卷二十载陈太建九年(577年)“七月庚辰,大风雨,(雷)震(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华表。”等。但这些倒塌损坏的华表多还掩埋于神道上,如近年我们在梁临川王萧宏墓神道、梁南平王萧伟墓神道上都勘探发掘出墓表及其顶部雕刻复瓣莲花的圆盘。
[8]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7、364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9]参见《宋书·礼志一》、《通典·礼典》、《六朝事迹编类》卷一引《通典》、《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引《建康实录》、《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一、元末宋濂《游钟山记》(收入[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一书)等书。
[10]南朝定林寺遗址位于钟山一号坛右下方山谷中,遗址附近尚存宋乾道元年至六年(1165~1170年)间一批摩崖题刻,如“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洋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乾道丁亥八月十日,叔涣、伯玉、中父、子云、无咎、伯山、方叔来游钟山,携八功德水,过定林烹茶乃还”等。另参见《首都志》(中正书局,1935年版)卷三。
[11]“重坛”一词出于《历代宅京记》卷七引《续汉书》。
[12]地坛有”南出陛”,见《唐会要·卷十上·杂录》。
[13]南朝早、中期,“南北二郊,一限南向”,见《南齐书·礼志上》。
[14]明洪武初,在京师筑“大祀坛”祭祀山川、四渎、五镇等,其功能相当于“地坛”,在坛门内设“海子”(方形水池),位置与一号坛上的石坑相同。《续汉志·郊祀志中》载,东汉北郊坛也有“海在东”之说。明代“大祀坛”设“海子”的做法是否有更早的历史渊源,值得研究。明“大祀坛”图见《洪武京城图志》十八。
[15]一号坛瓦当多出土于南部,尤其是板瓦、筒瓦等主要见于南面中部阶道(南陛)两侧。阶道西侧第二个坛层上又有砖铺遗迹,结合历史文献,我们分析这些瓦件可能是“坛门”倒塌后的遗存,惜在发掘中未能发现坛门梁柱遗存。刘宋南郊坛南有“坛门”一说,见《宋书·礼志一》载,祭拜(南郊)者“直南行出坛门”。按“北郊”礼仪多同“南郊”,故根据遗迹现象,我们认为现发现的一号坛南陛出土较多建筑遗物处可能为坛门所在。
[16]见《晋书·礼志》。
[17]见《陈书·高祖本纪》及《景定建康志》。
[18]《宋书·礼志一》。
[19]《宋书·礼志四》。
[20]《宋书·礼志一》载:“南郊……夕牲……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北郊,斋、夕牲、进熟及乘舆百官到坛三献,悉如南郊之礼……”
[21]参见清刘世珩《南朝寺考》卷二、卷三。
[22]参见《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第一、二部分该文注21,论文收录贺云翱著《历史与文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
[23]贺云翱、阮荣春等《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24、图22,文物出版社,1994年
[24]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第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另见林茂雨、李龙彬《高句丽民族的婚丧习俗及宗教信仰》,《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25]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
[26]“钟山北原”或“钟山北京”与六朝以来史书上又称“钟山北岭”、钟山“北高峰”、“北阜”、“北隐”、“北山”等相通,参见齐孔稚圭《北山移??文》、梁沈约《登钟山诗》、《建康实录》十四、《通典·礼典》、《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六朝事迹编类》卷四、清《重刊江宁府志》卷六等书。古代文献中所讲的“钟山北原道”或是指六朝时“钟山北岭”南麓定林寺后的一条登山道路。
[27]刘宋孝武帝在位时于礼制建设方面多有创举,除改作南、北郊坛外,还为仲尼开建庙制同诸侯之礼(大明元年,457年);始制朔望临西堂接群下受奏(大明二年);使六宫嫔妃修亲桑之礼(大明三年);躬耕藉田(大明四年);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改建明堂,拟则太庙(大明五年);置陵室,修藏冰之礼(大明六年);为京都始在博望梁山立双阙(大明七年)等。或复古制,或有新创,钟山北郊坛之规制应与其人有关。参见《宋书·孝武帝本纪》、《宋书·礼志》、《隋书·宇文恺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宋纪十一》。
[28]参见王仲奋《地坛史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29]有关资料见《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七《礼仪部六·郊丘》引各书、又见《后汉书·郊祀志》、《晋书·礼志》、《宋书·礼志一》、《唐会要·卷十》等。
[30]按礼书所载,北郊坛应为“方坛四陛”,但钟山一号坛仅见“南陛”,除坛北面被民国时期修建军用公路而破坏导致北陛等结构不清外,其东、西两面皆无“陛”发现。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姜波博士研究,东汉北郊坛坛制为一重,四陛,外有墙,而钟山一号坛有4个坛层、无壝墙发现。此外,钟山南朝刘宋北郊坛所在位置也偏高,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部分不符,其原因值得研究。参见《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续汉书·祭祀志中》叧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第二章第二节。
本文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7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